天刚下过一场小雨。清新的泥土味中夹杂着异香,韩昉忍不住打个喷嚏,长「吁」一声。胯下的枣红色瘦马似乎误解主人的命令,停住了马步。韩昉小腿发力,夹了夹马肚。瘦马抬起马蹄,慢吞吞地往前挪动。
「韩状元,昨天我就一直在纳闷,你放着我给你准备好的战马不骑,偏偏要骑这头农家拉磨用的劣马,这种马放马市上,十贯铜钱都不值。」萧容说道。
「咱们这次是去求和,又不是去娶亲游街,骑那么好的马干什么?」韩昉说道。
「为什么求和就不能骑好马?」萧容问道。
「不是求和不能骑好马,而是去跟宋国求和时最好不要骑好马。」韩昉答道,「跟咱们大辽国的马相比,宋国的马匹普遍瘦弱矮小,这些年来他们一直想要繁育出可堪一用的高头大马,却从未成功,这是他们宋国朝廷多年的心病。要是我也骑着一匹像你胯下骑着的骏马去见宋国人,莫不是要成心激怒他们?」
「韩状元,你不早点说!」萧容说道,「早知道我也骑一匹劣马来了!」
「萧相公,这你就不懂了吧?我骑劣马,你反倒要骑骏马。」韩昉说道,「你现在骑的这匹白马就很合适,毛色发亮,肌腱饱满,高大威猛,很好很好。」
「这又是为什么?」萧容问道。
「为了不让宋国人轻视咱们。」韩昉说道,「为了向宋国表明,咱们大辽国虽然虎落平阳,但虎威犹在。」
「没想到其中还有这番道理。」萧容叹气道,「韩状元不愧是出身于外交世家,办事老练又有计谋。」
前面就是宋军军营。一座方形帐篷外,摆着一张长桌,两旁插着十来面大黄龙负图旗。旗帜上的火焰脚迎着细风,微微摆动。
远远走来一个约七尺高的大汉。他穿着红色战袍,头戴一顶凤翅盔,走路时两脚向内形成「八」字。一百来个穿着甲胄的亲兵寸步不离地跟在大汉身后。
韩昉和萧容同时下马。韩昉作了一个叉手礼,对大汉说道:「好久不见,恭喜童相公高升太师!」
「好久不见,韩相公的消息还是这么灵通。」童贯笑道。
「童太师,有问题咱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嘛。」韩昉说道,「何必兴师动众,带这么多人来呢?」
童贯打量了一眼身旁的亲兵,笑道:「这还叫人多?大部队还在城里呢。韩相公,你猜我这次出征,带了多少人?」童贯笑眯眯地盯着韩昉,右手搓捻着下颌稀疏泛白的胡须。
「我猜最少也有二十万人——童太师,这是何必呢?」韩昉说道,「自澶渊之盟以来,咱们南北两朝——大宋国和大辽国,百年来情同手足,何以今日却兵戎相见?怕是有阴谋家从中作梗,挑拨你我两国的兄弟情谊。俗话说,鹬蚌相争,渔翁得利,童太师切莫上当。」
「我上当?我清醒得很呢。」童贯冷笑一声,「今时不同往日,如今我大宋兵强马壮,国富民强,岂是你辽国能比的?你小小辽国也配跟咱称兄道弟?」
「童太师,要怎样才肯退兵呢?」韩昉问道。
「退不了。」童贯说道,「韩相公,你以为出兵打仗是小孩子过家家,说出兵就出兵,说退兵就退兵的?」
「童太师,出兵伐辽这件事,你大宋可算是违约了。」韩昉转头看了一眼萧容,摆了摆手掌。萧容从怀里掏出一张约十寸长、七寸宽的羊皮纸,展开在童贯和韩昉的面前。
「童太师,这是一百多年前,你大宋国递交给我辽国的誓书,黄纸黑字,写得可是明明白白呢。」
「是吗?」童贯笑道,「我不识字,你给我念念。」
韩昉被童贯呛得说不出话来,脸颊憋得通红。良久,韩昉稍稍平复了心绪,见童贯仍旧笑嘻嘻地盯着他。
他凑近羊皮纸,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:「维景德元年,岁次甲辰,十二月庚辰朔、七日丙戌,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,共遵成信,虔奉欢盟,以风土之宜,助军旅之费,每岁以绢二十万匹、银一十万两,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,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。沿边州军,各守疆界,两地人户,不得交侵。或有盗贼逋逃,彼此无令停匿。至于陇亩稼穑,南北勿纵惊骚。所有两朝城池,并可依旧存守,淘壕完葺,一切如常,即不得创筑城隍,开拔河道。誓书之外,各无所求。必务协同,庶存悠久。自此保安黎献,慎守封陲,质于天地神只,告于宗庙社稷,子孙共守,传之无穷,有渝此盟,不克享国。昭昭天监,当共殛之。远具披陈,专俟报复,不宣,谨白。」
「韩相公,这纸上的一大段话,说的都是什么意思?我是穷苦人家的孩子,识字不多,不通句读,还望韩相公你这个文化人给我翻译翻译。」
「这纸上写的,正是百年以前,你大宋与我大辽结下的澶渊之盟。盟约的内容,是你们宋国每年给我大辽一笔岁币,我们两国互不出兵征伐,违背此盟,必遭天谴!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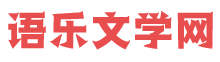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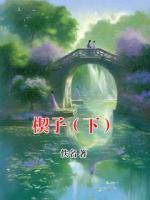
 错爱如烟花般易逝
错爱如烟花般易逝 老公在儿子满月宴,播放我的生产视频
老公在儿子满月宴,播放我的生产视频 邻居新婚当天,我用狗屎糊满婚车
邻居新婚当天,我用狗屎糊满婚车 老公嫌我家庭主妇拿不出手,我扭头空降他新上司
老公嫌我家庭主妇拿不出手,我扭头空降他新上司 婆婆让我生儿子?我让她儿子直接消失
婆婆让我生儿子?我让她儿子直接消失 慢慢讲
慢慢讲 未央夜风摇曳
未央夜风摇曳 不存在的自杀
不存在的自杀 抢了绿茶婊的三个竹马后
抢了绿茶婊的三个竹马后 离婚后清冷前夫追悔莫及
离婚后清冷前夫追悔莫及 炮灰女配黑化后,男主们跪求原谅
炮灰女配黑化后,男主们跪求原谅 别吵,朕在摸鱼
别吵,朕在摸鱼 金牌狂妃:我本倾城
金牌狂妃:我本倾城 绝世剑修
绝世剑修 隐形遗产
隐形遗产 一婚到底,错爱总裁
一婚到底,错爱总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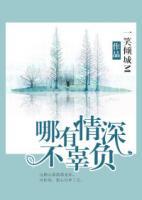 哪有情深不辜负
哪有情深不辜负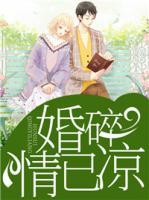 婚碎情已凉
婚碎情已凉 医者仁心
医者仁心 二小上山
二小上山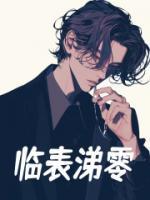 临表涕零
临表涕零 长白山神
长白山神 合租第一天,校花卡洗衣机里了
合租第一天,校花卡洗衣机里了 家族无敌,你配和我讲道理?
家族无敌,你配和我讲道理?
有一种上瘾,一旦爱上,便无法戒掉!我想我已经对小说《楔子(下)》彻彻底底上瘾了,更不可自拔的爱上了小说中的主角韩昉萧容,多么希望现实中也有这么一个人等着我!